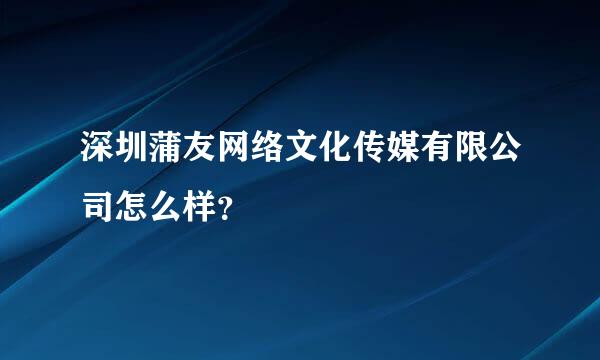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兄肢”,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谈伍动的人”。仅就“思想”而言,梁漱溟的最重要着作或许是1921年出版时就轰动一时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仅就“行动”而言,他的最重要着作或许是1937年出版的总结近十年乡治运动经验的《乡村建设理论》。但如果确实要把梁漱溟当作“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甚至如他期望的把他当作“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么1942年着手撰写、1949年6月完稿的《中国文化要义》,无疑是他最重要的着作。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说法,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他的其他着述一样,充满着“问题意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梁漱溟毕生思考的两大问题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每个人从少年起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中国文化本身,梁漱溟也从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人生态度,或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判断,在西方和印度都与宗教密不可分,而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在梁漱溟那里,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体”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道”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这个“器”的问题。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的时候虽然已经不像他写《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时候那么着眼于构造一个建基于人生哲学的覆盖全球的文化哲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仍然设法用“本能”、“理智”和“理性”这样一些西方人也能理解的概念来讨论问题。在梁漱溟那里,中国文化对一个有意义人生的重要性不限于中国一隅;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不只是因为它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重建所具有的工具价值。梁自己也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那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其及哲学》。1985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36年之后,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上作的讲演,题目也含尘或是“中国文化要义”。那时梁漱溟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对今天如何阅读《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这是一条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