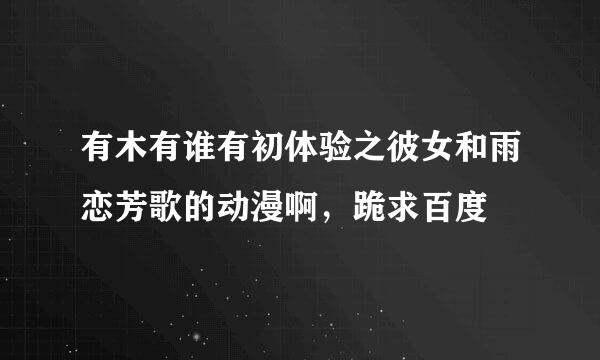1.黄昏了,太阳正落下地平线,辽阔的沙漠被染成一片血色的红。这时鼓声响了起来,它的声音响得很沉郁,很单调,传得很远,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是婚礼,这种神秘的节奏实在有些恐怖。我一面穿毛衣一面往罕地家走去,同时幻想著,我正跑进天方夜谭的美丽故事中去。赏析: 动静结合,用沙漠的色彩和鼓声衬出作者当时的心情2.“我不要,先给家,再来装修我,沙漠里用不著衣服。”他仍穿鞋底有洞的皮鞋上班。赏析: 一句话写出荷西朴实顾家的性格,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生活的艰苦。3.太阳像溶化的铁浆一样洒下来,我被晒得看见天地都在慢慢的旋转。赏析: 用当时的天气写出荷西的辛苦。4飞蛾扑火时,它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 一个女人已经刮得全身的黑浆都起来了,还没有冲掉,外面一间她的孩子哭了,她光 身子跑出去,将那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抱进来,就坐在地上喂起奶来。她下巴、颈子、脸上、 头发上流下来的污水流到胸部,孩子就混着这些污水渣歼大吸着乳汁。 我呆看着这可怖肮脏透顶的景象,胃里又是一阵翻腾,没法子再忍下去,转身跑出这个房间。一直奔到最外面一间,用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走回到铁丝上去拿衣服来穿。 "她们说你不洗澡,只是站着看,有什么好看?改晌"老板娘很有兴趣地问我。"看你们怎么洗澡。"我笑着回答她。"你花了四十块钱就是来看看?"她张大了眼睛。"不贵,很值得来。""这儿是洗身体外面,里面也要洗。"她又说。"洗里面?"我不懂她说什么。她做了一个掏肠子的手势,我大吃一惊。"哪里洗?请告诉我。"既吃惊又兴奋,衣服扣子也扣错了。 "在海边,你去看,在勃哈多海湾,搭了很多夏依麻,春天都要去那边住,洗七天。" 当天晚上我一面做饭一面对荷西说:"她说里面也要洗洗,在勃哈多海边。""不要是你听错了?"荷西也吓了一跳。"没有错,她还做了手势,我想去看看。"我央求荷西。从小镇阿雍到大西洋海岸并不是太远,来回只有不到四百里路,一日可以来回了。勃哈 多有个海湾我们是听说,其他近乎一千里的西属撒哈拉海岸几乎全是岩岸没有沙滩。车子沿着沙地上前人的车印开,一直到海都没有迷路,在岩岸上慢慢找勃哈多海湾又费 了一小时。 "看,那边下面。"荷西说。我们的车停在一个断岩边,几十公尺的下面,蓝色的海水平静地流进一个半圆的海湾里 ,湾内沙滩如竖上搭了无数白色的帐篷,有男人、女人、小孩在走来走去,看上去十分自在安详 。"这个乱世居然还有这种生活。"我羡慕地叹息着,这简直是桃花源的境界。"不能下去,找遍了没有落脚的地方,下面的人一定有他们秘密的路径。"荷西在悬 崖上走了一段回来说。 荷西把车内新的大麻绳拉出来,绑在车子的保险杠上,再将一块大石头堆在车轮边卡住 ,等绑牢了,就将绳子丢到崖下去。"我来教你,你全身重量不要挂在绳子上,你要踏稳脚下的石头,绳子只是稳住你的 东西,怕不怕?"我站在崖边听他解释,风吹得人发抖。"怕吗?"又问我。"很怕,相当怕。"我老实说。"好,怕就我先下去,你接着来。"荷西背着照相器材下去了。我脱掉了鞋子,也光脚吊下崖去,半途有只怪鸟绕着我打转 ,我怕它啄我眼睛,只好快快下地去,结果注意力一分散,倒也不怎么怕就落到地面了。 "嘘!这边。"荷西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落了地,荷西叫我不要出声,一看原来有三五个全裸的撒哈拉威女人在提海水。这些女 人将水桶内的海水提到沙滩上,倒入一个很大的罐子内,这个罐子的下面有一条皮带管可以 通水。一个女人半躺在沙滩上,另外一个将皮带管塞进她体内,如同灌肠一样,同时将罐子提 在手里,水经过管子流到她肠子里去。 我推了一下荷西,指指远距离镜头,叫他装上去,他忘了拍照,看呆了。水流光了一个大罐子,旁边的女人又倒了一罐海水,继续去灌躺着的女人,三次灌下 去,那个女人忍不住呻吟起来,接着又再灌一大桶水,她开始尖叫起来,好似在忍受着极大 的痛苦。我们在石块后面看得心惊胆裂。这条皮带管终于拉出来了,又插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内清洗,而这边这个已经被灌足了 水的女人,又被在口内灌水。 据"泉"那个老板娘说,这样一天要洗内部三次,一共洗七天才完毕,真是名副其实的 春季大扫除,一个人的体内居然容得下那么多的水,也真是不可思议。过了不久,这个灌足水的女人蹒跚爬起来,慢慢往我们的方向走来。 她蹲在沙地上开始排泄,肚内泻出了无数的脏东西,泻了一堆,她马上退后几步,再 泻,同时用手抓着沙子将她面前泻的粪便盖起来,这样一面泻,一面埋,泻了十几堆还没有 停。等这个女人蹲在那里突然唱起歌时,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特笑起来,她当时的情景非常 滑稽,令人忍不住要笑。荷西跳上来捂我的嘴,可是已经太迟了。那个光身子女人一回头,看见石块后的我们,吓得脸都扭曲了,张着嘴,先逃了好几十 步,才狂叫出来。我们被她一叫,只有站直了,再一看,那边帐篷里跑出许多人来,那个女人向我们一指 ,他们气势汹汹地往我们奔杀而来。"快跑,荷西。"我又想笑又紧张,大叫一声拔腿就跑,跑了一下回头叫:"拿好照 相机要紧啊!" 我们逃到吊下来的绳子边,荷西用力推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本事,一会儿就上到悬崖 了,荷西也很快爬上来。可怖的是,明明没有路的断崖,那些追的人没有用绳子,不知从哪条神秘的路上也冒出 来了。我们推开卡住车轮的石块,绳子都来不及解,我才将自己丢进车内,车子就如炮弹似的 弹了出去。 过了一星期多,我仍然在痛悼我留在崖边的美丽凉鞋,又不敢再开车回去捡。突然听见 荷西下班回来了,正在窗外跟一个撒哈拉威朋友说话。"听说最近有个东方女人,到处看人洗澡,人家说你--"那个撒哈拉威人试探地问荷西。"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太太也从来没有去过勃哈多海湾。"荷西正在回答他。我一听,天啊!这个呆子正在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连忙跑出去。"有啦!我知道有东方女人看人洗澡。"我笑容可掬地说。荷西一脸惊愕的表情。"上星期飞机不是送来一大批日本游客,日本人喜欢研究别人怎么洗澡,尤其是日本女 人,到处乱问人洗澡的地方--"荷西用手指着我,张大了口,我将他手一把打下去。那个撒哈拉威朋友听我这么一说,恍然大悟,说:"原来是日本人,我以为,我以为… …"他往我一望,脸上出现一抹红了。 "你以为是我,对不对?我其实除了煮饭洗衣服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你弄错了。""对不起,我想错了,对不起。"他又一次羞红了脸。等那个撒哈拉威人走远了,我还靠在门边,闭目微笑,不防头上中了荷西一拍。"不要发呆了,蝴蝶夫人,进去煮饭吧!" 吃过饭后我们在天台上坐着,那夜没有风,荷西叫我开灯,灯亮了,一群一群的飞虫马上扑过来,它们绕着光不停地打转,好似这个光是它们活着唯一认定的东西。 我们两人看着这些小飞虫。 “你在想什么?”荷西说。 “我在想,飞蛾扑火时,一定是极快乐幸福的。” “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家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学撒哈拉威人一辈子坐在席子上?” “因为我们不是他们。” “我为什么不能改,我问你?”我抱住三块木条再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荷西笑起来。 “那是宗教的问题,不是生活形态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爱吃骆驼肉?基督教不可吃骆驼吗?” “我的宗教里,骆驼是用来穿针眼的,不是当别的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家具才能活得不悲伤。” 那个下午,我整理海运寄到的书籍纸盒,无意间看到几张自己的照片。 一张是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的大衣,头发梳上去,挂了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 另外一张是在马德里的冬夜里,跟一大群浪荡子(女)在旧城区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红酒,我在照片上非常美丽,长发光滑地披在肩上,笑意盈盈—— 我看着一张一张的过去,丢下大叠照片,废然倒在地上,那种心情,好似一个死去的肉体,灵魂被领到望乡台上去看他的亲人一样怅然无奈。 沙是一样的沙,天是一样的天,龙卷风是一样的龙卷风,在与世隔绝的世界的尽头,在这原始得一如天地洪荒的地方,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民族自决这些陌生的名词,在许多真正生活在此地的人的身上,都只如青烟似的淡薄而不真实罢了。 “这儿是我的土地,我父母埋葬的地方。”沙依达的眼光突然朦胧了起来,好似内心有什么难言的秘密和隐痛,她竟痴了似的静坐着忘了再说话。 “你呢?三毛?”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我。 “我是不想走的,我喜欢这里。” “这儿有什么吸引你?”她奇怪地问我。 “这儿有什么吸引我?天高地阔、烈日、风暴,孤寂的生活有欢喜,有悲伤,连这些无知的人,我对他们一样有爱有恨,混淆不清,唉!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如果这片土地是你的,你会怎么样?” “大概跟你一样,学了护理医疗,其实——不是我的和是我的又怎么分别?”我叹息着。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撒哈拉了,也只有对爱它的人,它才向你呈现它的美丽和温柔,将你的爱情,用它亘古不变的大地和天空,默默地回报着你,静静地承诺着对你的保证,但愿你的子子孙孙,都诞生在它的怀抱里。 不偷生苟活,就去流亡吧! 我的朋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而今也不曾相逢,但是人生相识何必相逢,而相逢又何必相识。 在台北,我不觉得离你们近,在非洲我也不觉得离你们远,只要彼此相知欣赏,天涯真是如此比邻啊! 我虽然常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指路星,却是我的神。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 因为上帝亘久不变的大爱,我就能学习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