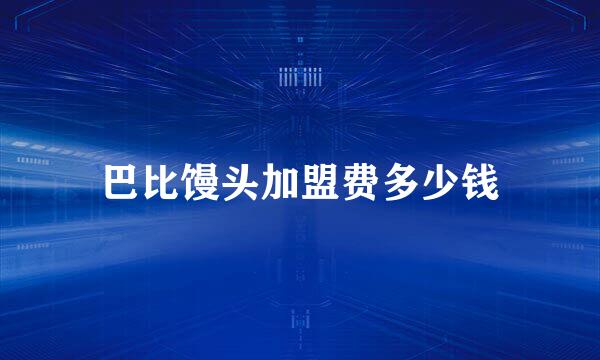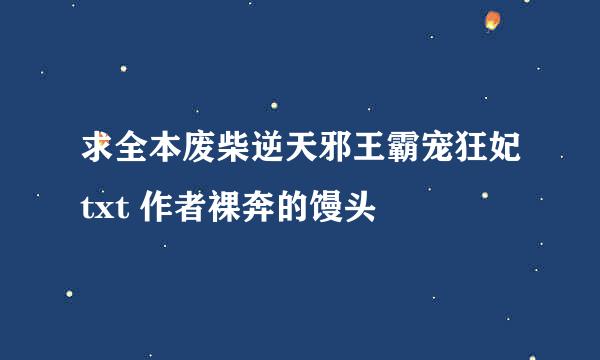《不名堂重读红楼札记》之廿 《石头记》里有一个焦大,只出了一次场,还被喂了一嘴的土和马粪,但他那句“醉骂”却让读者散姿销过目不忘:“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冲游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里藏。”(第七回)“爬灰的爬灰”,指的是贾珍和秦可卿这对爷媳,就是作者不在前文交代“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咱们也可从秦可卿死后她公公那副丑陋嘴脸上看出来;至于“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情况就不那么明了了,多数人也只能猜测或许是宝玉和凤姐这对叔嫂——之所以是“猜测”,是因为《石头记》有关于兹的笔墨少得可怜,几乎成了无隙可乘的“疑案”。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小说情节在《石头记》里并不罕见,作者在第十五回“秦鲸卿得趣馒头庵”里做得更绝,基本上是直接“杜门”—— 馒头庵里那笔“糊涂账” 第十五回的回目全称是“王熙凤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得趣馒头庵”部分写秦钟在为姐姐秦可卿送葬时“半路‘邪’出”,来到水月庵和智能儿鬼混: 谁想秦钟趁黑无人,来寻智能。刚到后面房中,只见智册孝能独在房中洗茶碗,秦钟跑来便搂着亲嘴。智能急的跺脚说:“这算什么呢?再这么,我就叫唤了。”秦钟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儿再不依,我就死在这里。”智能道:“你想怎么样?除非等我出了这个牢坑,离了这些人,才依你。”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救不得近渴。”说着,一口吹了灯,满屋漆黑,将智能抱在炕上,就云雨起来。那智能百般挣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见一人进来,将他二人按住,也不则声。二人不知是谁,唬的不敢动一动。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听声,方知是宝玉,秦钟连忙起身,抱怨道:“这算什么!”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咱们就叫喊起来!”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钟出来道:“你可还和我强?”秦钟笑道:“好人!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你要怎么样,我都依你。”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凤姐在里间,秦钟、宝玉在外间,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铺、坐更。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第十五回。下文未注出处者同) 曹雪芹的“杜门”意识体现在“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二十七字上。为证明这确属疑案,脂砚斋也不失时机地在文后题批附和:“忽又作如此评语。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如不如此隐去则又有何妙文可写哉?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笔。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隐事,借石之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丘壑在焉。” 尽管作者和批者都说“未见真切”,后续情节不好纂创,但本次阅读,不名堂主还是发现了两大异常:一是脂砚斋“话中有话”——曹雪芹有“无限丘壑”的“大奇笔”,如果的是未见著文字,批评者所称的“最妙之文”岂不空口无凭?“隐去”分明是“蒙蔽”,并不是曹雪芹没写!二是曹雪芹的“欲言又止”——“不敢纂创”的故事情节凡小说作者都会回避,假如作者真的不想让读者知道宝、秦二人算何账目,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写,曹雪芹有必要画蛇添足说明“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么? 不名堂主觉得,惜墨如金的曹雪芹在此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多写二十七字,就是要制造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阅读效果,让读者自行追索宝玉与秦钟“到底要算什么账?” 尽管心存疑问,之前每每读完普及版《红楼梦》,不名堂主还是“一头雾水”,那个版本没有脂砚斋批语,也就看不到这位“神秘人士”所强调的“云烟渺茫之中”的“无限丘壑”,便渐渐按照曹雪芹的字面意思将其视为馒头庵里的一笔“糊涂账”。但本次阅读稍有不同,咱将着重点转到当事人贾宝玉的行为上来,因为怡红公子在馒头庵里的行止实在太耐人寻味了—— 面对做爱场面心如止水,宝玉可能么? 这是从心理学最浅层提出的疑问。 谁都有过青春期,每个少年都做过让内裤燃烧得水渍斑斑的春梦,然后才成为男人,为什么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就和咱们常人如此不同呢——面对秦钟和智能的做爱场面,他居然能心如止水!宝玉不是布尔什维克,他是有“前科”的,也不是不懂人事的“黄花闺男”,且距“阳痿”、“更年期”远着呢,一只偷吃过鱼的小猫面对一盘腥膻大餐竟然无动于衷,他的心理素质是不是忒好了点儿? 而他的行为又如此怪异:摁住了正在动作的这一对偷情“鸳鸯”! 会不会是秦钟“一口吹了灯,满屋漆黑”,曹雪芹借“未见真切”而故意不写宝玉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呐? 这好办,咱们回到秦钟吹灯前,看看曹雪芹(同等重要的还有脂砚斋)“提供”给咱们的是怎样的一个贾宝玉: 首先咱们看到村姑二丫头已经让宝玉“砰然心动”。这是送葬途中的一个插曲,有三个地方可以窥见宝玉“春心萌动”:一是看红衣少女二丫头摆弄纺车时,秦钟悄语“此卿大有意趣”,宝玉并未正颜厉色,而是将秦钟“一把推开,笑道:‘该死的,再胡说,我就打了。’”脂砚斋在此及时批出宝玉的暧昧心态:“的是宝玉性生之言”——“性生”者,“性冲动萌生”是也!二是二丫头“丢下纺车,一径去了”后“宝玉怅然无趣”,脂砚斋再次适时题批:“处处点情。又伏下一段后文。”——“又伏下一段后文”暂且放过,“处处点情”已经说明宝玉被“点燃”了;三是离开时,“只见迎头二丫头怀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料是众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争奈车轻马快,一时展眼无踪。”脂砚斋在“展眼无踪”后批下的五个字异常醒目——“四字有文章。” 其次咱们发现宝玉不想回家,已心存“野意”。“吃个野意儿”(第三十九回)是刘姥姥的话,借来形容不想回家的宝玉非常合适。傍晚的铁槛寺,“邢、王二夫人知凤姐必不能回家,也便就要进城。王夫人要带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凤姐住着。王夫人无法,只得交与凤姐,便回来了。”——这里没有脂砚斋批语,但有作者埋下的关键字眼,且这个“关键句”与“吃个野意儿”密切相关! 再次咱们明白小尼姑智能儿已将宝玉“撩拨”得“入画”了。此时的智能儿还衣衫齐整,是秦钟吹灯前的智能儿,“因见智能儿越发长高了,模样儿越发出息了”,宝玉想起了一个激情画面——在贾母房中,秦、智二人曾经搂着亲嘴,“我叫他到的是无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到的是有情意的”,宝玉非要通过秦钟让智能儿倒茶的这句说辞,已然暴露他渐渐“入港”了。 这一路“潜移默化”,说明宝玉就是一个超正常的“邻家少年”,但待到将相向而叠的秦钟和智能儿按于掌下,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很心无杂念了,很波澜不惊了,很布尔什维克了,可能吗?不是不名堂主喜说大话,如果能见度良好,咱们看到的贾宝玉说不定比被平儿“浪上火来”只能“弯着腰”(第二十一回)说话的他堂哥贾琏还要不堪呐。 所以不名堂主认为,曹雪芹这一大反人性、大悖常理的情节设计,是有意隐去宝玉的“不堪”,是为后文的“算账”腾挪想象空间,“如不如此隐去则又有何妙文可写哉?”脂砚斋已一语戳穿小说作者的文字把戏! 但无论怎样“不堪”,咱们读者起码是要了解个大概的。 《石头记》描写宝玉冲击偷情“鸳鸯”的情节共有两处,除此之外,他还于不远的将来脚踢房门惊散了焙茗和卍姑娘(第十九回)。比较而言,“惊散茗卍”貌似不期而遇,“拆开秦智”无疑是有意而为——咱们不难想象怡红公子鬼鬼祟祟的跟踪过程,因为他掌握秦钟和智能儿“有一腿”的过往,也知道秦钟说出“此卿大有意趣”后的即时心态。 但宝玉的“即时心态”咱们多数读者似乎没有很好把握:惊散茗卍时,宝玉第一时间想起了与他“同领警幻之训”的袭人,并立马“要挟”焙茗第一时间带他面晤回家的“花姑娘”;那么拆开秦钟和智能儿后,宝玉是否也会思想起某位与其有过“云雨”事实的“姐姐”抑或“妹妹”呢? 倘若曹雪芹如此安排情节就是在“诱导”咱们读者作如此联想,那“某个人”太好确认啦,就像现今高档次选举只有一名候选人一样,当晚的馒头庵只住着一位姐姐—— 王熙凤到底是“弄权铁槛寺”,还是“得趣馒头庵”? 那就是凤姐! 说到凤姐,绕不过的话题便是“弄权铁槛寺”,因为曹雪芹就是这么“题目”的;说到“弄权”,绕不过的话题便是她和老尼静虚合谋,间接致死金哥二人,直接受贿三千银子,因为这是凤姐劣迹的肇始,“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第十六回);说到“铁槛寺”,绕不过的话题便是……绕不过的话题……绕不过的……不名堂主真的绕不过去了,说不下去了:因为这里出现了“错位”——凤姐接受老尼托请“恣意弄权”的地点不是馒头庵么,怎么成了铁槛寺了? 凤姐在铁槛寺“弄权”了么?很遗憾,她在铁槛寺的言行中规中矩,既没致人死命亦未受贿银两——她只是嫌在铁槛寺下榻的族人太多,“不方便,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净虚说了,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而已。如果“嫌铁槛寺不方便、另辟水月庵下榻处”也算“弄权”,相对馒头庵“致人死命、违法受贿”而言,恰是“纱筛”与“石磨”的比重关系——曹雪芹言重了!那么“不留‘未密之缝’”的曹雪芹为何要留下这一“错位”呐?也就是说“披阅十载”的芹溪居士为何如此“题目”呐?只有一种解释:在小说作者看来,凤姐在铁槛寺的“不方便”,和“弄权馒头庵”致人死命以及违法受贿一样“兹事体大”! 解析铁槛寺和馒头庵两处“决定”一样重大的关键,应该是当事人夜宿馒头庵前夕的“临床表现”。现在咱们再来看看凤姐的言行: 一是邀宝玉同车——“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这是凤姐送别好姊妹秦可卿最后一程时和宝玉说的第一句话,曹雪芹为其开出的“理由”既堂皇又得体:“凤姐因记挂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话,贾政管不着这些小事,惟恐有个闪失,难见贾母。”于是宝玉就合情合理地下马“爬入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进”,“说笑”些啥?没有文字!曹雪芹只给出结果:仪式完成后王夫人要带宝玉回家,宝玉不走——“只要跟凤姐住着”。二是收通灵玉入房——小说作者在复述宝玉和秦钟“算账”前这样描写:“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凤姐在里间,秦钟、宝玉在外间,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铺、坐更。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 我们发现,凤姐将原本的“姐弟”(严格来说应该是“叔嫂”)说成“姐儿”了——为了“姐儿”二字不显突兀,曹雪芹还让凤姐先行铺垫一句“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就当下的阅读效果看,曹雪芹蒙混过关了,诡计得逞了,因为“姐儿”之下的事理似乎没有多少读者追问!“叔嫂”和“姐儿”最显著的区别是“性”——前者是两性关系,后者是单性关系。凤姐将称呼这么一改,其效果相当“掩耳盗铃”:抹杀“性”的存在!从道德层面看,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姐儿”是可以同床共枕的,而“叔嫂”不可以,像凤姐和宝玉这样有性经验的“叔嫂”尤其不可以。 分析至此,不名堂主终于发现了奥妙:曹雪芹让凤姐改称呼实际上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隔壁阿二不曾偷”的意蕴立马显山露水了——那句充满野趣的“只要跟凤姐住”,明显是“只要跟凤姐睡”的婉转说法,而后面的“拿来(通灵玉)塞在自己枕边”——“通灵玉”本来就是“宝玉”! 将凤姐的心思和宝玉的“不堪”稍一联系,不名堂主很想说出一个事实:隔壁的阿二曾不曾偷银子咱们不管,里间的阿凤可是实实在在偷了小叔子了,而且明显是干柴遇上烈火,完全两厢情愿。 事实上,为了凤姐能顺利偷到宝玉,曹雪芹在前面起码作了两处铺垫:一是“协理宁国府”诸事完成后,凤姐有“放松放松”的心理需求;一是贾琏送黛玉出远门时日较久,凤姐有“放纵放纵”的生理要求。 “家事消亡首罪宁”,“次罪”必然落到荣国府。反应到“乱伦”方面,宁国府贾珍“爬灰”在先,荣国府凤姐“养小叔子”居后,这符合某种序次关系。在《石头记》里,曹雪芹将“淫乱”列为贾府败落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一层面看,凤姐借“不方便”之口在铁槛寺作出的“下榻馒头庵”决定,表面上“弄权”成分微乎其微,但行了“养小叔子”之实就性质恶劣,故完全可以等同致人死命与违法受贿,也就是说曹雪芹完全可以如此“题目”。 现在大家应当明白两件事了:一是曹雪芹的这种写法收到了一石双鸟的效果——既写了凤姐弄权铁槛寺、又写了凤姐在馒头庵弄权,既写了秦钟和智能儿得趣馒头庵,又写了凤姐和宝玉在馒头庵得了“野趣”(野合之趣)——凤姐“弄权铁槛寺”,就是为了自己“得趣馒头庵”;二是宝玉和秦钟的“算账”实际上是一种“安排”——宝玉两次冲散得趣的“鸳鸯”,使秦钟和焙茗的“好事”都成了“半拉子工程”,他得有适当的补救措施才像“宝玉”,焙茗是他的小厮倒可以摆出主子的威仪不予理睬,秦钟是“同志”加“兄弟”还加“情友”(第九回回目),必须有所安慰,比如腾出外间让秦钟和智能儿继续完成工程的另一半,同时让自己沦为“失床者”,给凤姐一个充分的理由显示爱心将自己“塞在枕边”,等等。 可惜的是,前面都是不名堂主的推理,如果有曹雪芹的原文证明就圆满了。 也许有朋友要问:作者不是写了“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铺、坐更”么,王熙凤有这么大胆在众目睽睽下“偷小叔子”?有此一问的朋友太小看凤姐的色胆包天了,后文“审兴儿”一节可以拿来佐证;况且这是送葬途中,不是什么盛大派对,身边只有几个心腹小厮而已,曹雪芹那句“满地下皆是”是用来“瞒人”的。也许认定“《石头记》就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的朋友还会置疑:曹雪芹会把自己的化身贾宝玉写得如此污秽不堪吗?这不是自爆其丑?曹雪芹情何以堪!对此,不名堂主只能如此回答: 是的,曹雪芹笔下的这对荣国府叔嫂,在馒头庵就是这么肮脏—— “拿耳挖子剔牙”很肮脏,也很黄 “拿耳挖子剔牙”的情节出现在距“得趣馒头庵”十三回后的第二十八回,如果要计算距离,大约是北京到河内的长度,但原文很短: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凤姐院前,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小子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正好!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房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来,向宝玉道:“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上用纱各色一百匹,金项圈四个。”宝玉道:“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凤姐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听说,只得写了。 这一细节描写给人的第一感觉无疑是肮脏不堪。凤姐是荣国府的实力派当家人,出身也算大家闺秀,她的作派怎么可以和最为愚昧落后地区最不讲究的疯婆子一样污秽呢?纵览《石头记》其他文字,这一动作和凤姐的一贯作派大为不榫,基本是孤例。再对照二十八回前后文,这一细节与上与下均无必然联系,可谓真正的“枝蔓细节”,完全可有可无,难道是以炼字著称的曹大才子忽然“打盹”了? “拿耳挖子剔牙”,让不名堂主想起读高中时的一件陈年旧事——那时我们到区里的一家糖厂“学农”,一个同学晚上在垛场外听到甘蔗堆深处有两个女人对话。一个问:“男人的滋味到底是怎样的?”另一个答:“嗨!和掏耳朵一样样。”这位同学向大家学说后,我们猜测问者为闺女答者系少妇,她俩的对答让当晚的同学们乐不可支。 人的头部有七窍,也就是七个窿窿,曹雪芹是借耳孔和耳挖的关系为女人和男人的关系设譬?如果确定,那“拿耳挖子剔牙”又“错位”了——鼻子底下的窿窿接纳错了对象,有可能是暗喻“乱伦”。不名堂主作速返回馒头庵,逐字逐句进行比照。嗨!果然不愧为大师,曹雪芹“太有才了”——尽管相隔了十三大回,“拿耳挖子剔牙”就是“得趣馒头庵”的情节延伸,不但用来比喻凤姐和宝玉这对“叔嫂”乱伦的“嘴巴和耳挖”极尽熨贴,而且其他衔接文字亦无比妥当——尽管很污糟,尽管有点黄,尽管梦阮先生略嫌“下作”: 一、“凤姐蹬着门槛子”,“门槛子”指示“铁槛寺”。 二、二十八回宝玉的“这算什么?”和十五回秦钟的“这算什么?”是“接头暗号”,说明相隔十三回的两段文字是一“共同体”。 三、二十八回宝玉的“又不是账”,否定了十五回他自己所说的“再细细的算账”之“账”,以及作者曹雪芹的叙述句“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之“账目”,同时也说明不名堂主之“‘算账’即‘安排’”的推想成立。 或许又有朋友要质疑了:曹雪芹自己都说“未见真切,不敢纂创”,你这个什么堂主就看得如此分明?不是纂创?非常感谢此类提问,更无比感激“才鬼”曹雪芹的料事如神,二百多年前他就做好了回答,根本用不着别人越俎代庖—— “……怎么个写法?”“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在前面那节引文里,这是宝玉和凤姐的问答;在《石头记》文本之外,这是作者在与读者互动——凤姐“养小叔子”与贾珍“爬灰”一样,都是臭烘烘的“不堪”丑事,更何况还牵涉到主角宝玉,假如直笔明写,势必造成一定范围的“玷污”,届时书上方正正的汉字情何以堪?读者清亮亮的眼眸情何以堪?再者,既然写贾珍“爬灰”的天香楼一节“删除”了,那么写凤姐“养小叔子”的馒头庵一节是否也要“隐去”为宜?同理,既然“爬灰”事项在可卿的判词里(第五回)有所“逗漏”,那么“养小叔子”事项在凤姐的言行(具体由肢体语言“拿耳挖子剔牙”表现)上是否也要有所“保留”?不名堂主对芹溪居士这种“明写秦钟得趣,暗拟凤姐风流”的小说手法和他“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态度欣赏无比,同时觉得他对糊涂读者“横竖我自己明白,你不懂是你的事”的狂狷与“白眼相向”酷毙了——脂砚斋所指的“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笔”,应该包括前述成分。 凤姐“养小叔子”的事情坐实后,“得趣馒头庵”里的“账目”结清了么?没!从凤姐和智能两个女人对宝玉和秦钟两个男人互有好感、凤姐又作决定“越性辛苦一日”(按:好好理解这六个字)在馒头庵多住一天、以及秦钟染病而夭和守备之子投河而尽的对应关系等系列事件看,“得趣馒头庵”一回依然存在“糊涂账”,不名堂主目前也是“未见真切,不敢纂创”,且听以后的读书笔记再予解析。